让爱流动——海淀区第10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赵嘉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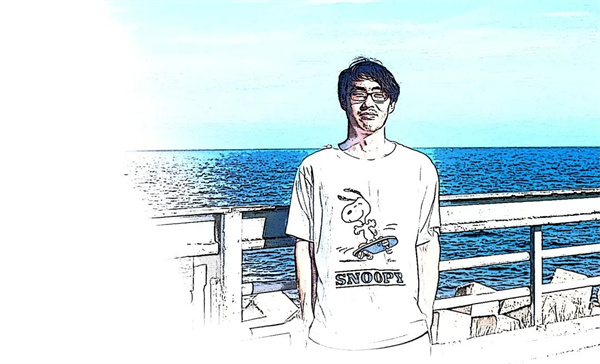
赵嘉鹏,男,1997年生人,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所在读研究生,2021年11月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期待奉献
父母将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加诸于儿女,这类事情在社会上饱受诟病,孩子们显然也多不情愿。而赵嘉鹏不同,他不但欣然接过并实现了妈妈未了的心愿,所行之事还一时传为美谈。
2020年6月,赵嘉鹏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完成,毕业的事情基本告一段落,按说应该拥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去走访大好河山,无奈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着,赵嘉鹏只好将自己封闭在河南的家里。
那天,赶巧嘉鹏妈妈也在家,她无意间看到红十字会的流动献血车就停在家门口的街上,赶紧喊嘉鹏:“快,跟我出去献血去。”本来就一直想献血的嘉鹏答应得也痛快,二话没说跟妈妈出了门。顺利献完血,医生问嘉鹏要不要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那时候,嘉鹏对中华骨髓库还没有太多了解,但因为受妈妈影响,至少知道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自己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大可放心。“再说,还能帮助一个病人,为什么不做呢?”赵嘉鹏很轻松地说,随后填写了《志愿捐献者同意书》和《志愿捐献者登记表》。
在一些人看来,捐献造血干细胞与献血可不同,神秘又有些不可预测,多少会感到恐惧,所以好奇地问赵嘉鹏是否一时冲动填了表,有没有后悔过。赵嘉鹏一笑:“怎么会后悔呢,现在主动献血的年轻人很多,一般只要献血的话都会加入中华骨髓库,很正常啊!”
这番话说得人们不禁感慨,如今的年轻人真不一样,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做这么大的决定没有感动,没有感慨,甚至似乎连勇气都不需要。做就做了,有什么呢?
对于这个决定,嘉鹏妈妈予以了充分的尊重和鼓励。原来,嘉鹏妈妈是医院里的护士,作为医务工作者,出于职业本能地拥有一颗悬壶济世之心,每天和病患打交道,见多了病痛折磨的她希望这世界上的病人越少越好。嘉鹏妈妈献过血,也登记加入过中华骨髓库,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配型成功,眼看着医院里的同事成功捐献,心里实在羡慕。四十岁之后,嘉鹏妈妈出现贫血,连献血机会都没有了,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儿子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她当然全力支持。
登记中华骨髓库之后,赵嘉鹏关注起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件事。他了解到,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可治疗恶性血液病,部分恶性肿瘤,部分遗传性疾病等75种致死性疾病,包括急性白血病、慢性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些患者从亲缘关系中寻找供髓者较容易,然而现代社会,家庭范围正在缩小,绝大多数的患者还是需要非血缘关系捐献者,由此可见,公民捐献造血干细胞多么重要多么有意义。赵嘉鹏又看了一下网络资料,到2019年11月,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突破9000例,中国红十字会还为此在山东举行了庆祝活动。9000例,这个数字相对于全国亟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来说并不算一个大数字。中华骨髓库目前约有30万库容量,而我国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有一百多万,现在的库容量仅能满足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患者需要。想到自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捐献者去救助一个生命,赵嘉鹏充满期待
如愿以偿
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也就半年时间,2021年2月份的一天,赵嘉鹏接到通知,告知他通过了初筛,已经配型成功。他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简直太幸运了,妈妈可是等了二十多年也没等到啊!
赵嘉鹏很兴奋,他知道高筛就是要对他们这些通过初筛的志愿者进一步进行筛选,选出一个匹配率最高的。几天后,赵嘉鹏到当地红十字会抽了血,交到省里去做高筛。又等待了三个月,5月初,嘉鹏接到通知,说高筛已通过,准备安排后续计划。这时候,赵嘉鹏已经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所读研究生了,他虽然很激动,但没有办法回到家乡河南进行下一步,于是河南红十字会很快将赵嘉鹏的信息和其他相关资料转到了北京红十字会。
六月,赵嘉鹏在北京做了体检,各项身体指标正常。原本以为马上就可以开始捐献,不想又盼了好几个月,一直到11月初才接到正式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通知。后来才听说,拖了这么久,是因为接受捐献的患者病情不太稳定,不适合做手术,所以一直等到患者病情稳定下来才继续进程。
很快,赵嘉鹏被安排住进了空军总医院旁边的一家宾馆,开始注射造血干细胞动员剂。连续五天的时间,前三天每天打一针,最后两天打两针,那期间捐献者基本属于停工状态。医生说,人的造血干细胞平时大多在骨髓中,动员剂就是号召造血干细胞“加班加点”工作,多分离出一些造血干细胞,并释放到血液中。一般来说,一个志愿者捐献前,需要打9针左右动员剂。整个采集过程最难熬的就是这几天打动员剂的时候,倒也没有太多不舒适,只是人一直处于高烧状态,头有时候会晕一下,身体燥热,嗓子眼就像火烤般焦灼,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口渴,赵嘉鹏每一天都要喝上六七瓶水。
到了这个阶段,捐献者就不能退出了。每一名志愿捐献者都可能是救助患者的唯一希望,虽然过程中可以改变捐献决定,但是放弃捐献对患者来说将是沉重的打击。可见,加入中华骨髓库是对生命的承诺,更是神圣庄严的使命。在初筛和高筛阶段红十字会一次又一次跟捐献者确认,就是为了防止捐献者在最后的时刻悔捐,因为在采集造血干细胞当天,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医院里,患者会进入无菌仓,他的所有血细胞都会被杀死,然后等待着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输送进去。赵嘉鹏说:“前段时间有则新闻是关于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在捐献当天悔捐的,患者家属情绪特别激动,这是能理解的。我之前还听说过这类事例,所以哪怕你不捐都可以,就是不要悔捐,虽然悔捐在法律上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在道德上确实要受谴责,但凡一个有点良知的人都无法原谅自己。”
而那个将生命期待于自己的患者是谁,来自哪里,作为捐献者的赵嘉鹏并不知晓,只知道对方是个小孩子,将在上海那边的一个医院做手术。捐献在两年内要双向保密,捐献者在采集之后会写一封信留下鼓励的话给受捐者,如果对方想感谢一下捐献者会寄封信过来,其他就不会透露太多的信息,对方姓甚名谁是个秘密。在赵嘉鹏看来,这样保密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毕竟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在做好事,何必让人知道?何必期待感谢?
捐献的头天晚上,赵嘉鹏有些兴奋,特别盼望去体验这个过程,总是忍不住想:“哇,这种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经历的,十万分之一的概率被我碰上了,让我可以拥有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经历。”处于亢奋中的他辗转难眠。
特殊历程
11月11日,网络上热闹的“双11”充斥着孤独者的“脱单”表白和购物狂的疯狂下单。这一天,赵嘉鹏不到七点就起床了,之后赶到医院抽血,八点开始正式采集造血干细胞。
赵嘉鹏躺在医院病床上,连着橡胶管的粗大针头扎入手臂,一个进一个出,全身不得动弹,那种因期待而产生的兴奋,因兴奋而产生的紧张感大概就像我们第一次乘坐过山车时车子启动前一样。随着进程的开始,他的紧张感越发强烈,大约半个小时后,新鲜感减淡,他的情绪逐渐趋于正常,心态逐渐平和,紧张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对于整个过程会出现怎样的不舒适怎样的心理反应,赵嘉鹏是很明了的,因为中华骨髓库官方资料有清晰的讲述。让他感觉煎熬的是连续四五个小时全身不能动,还要一直在那儿等待指标到达一个满意的值,这就算对身体强健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身心考验。有那么久吗?当然有。采集10克造血干细胞需要抽200毫升混悬液,要走一万多循环。所谓循环就是抽一次血,血液在机器里面有一个过滤,把需要的干细胞血液过滤下来,再将其余血液输回捐献者体内,血液从机器上到捐献者身体里走一圈叫一次循环。一万多循环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且五个小时后,如果机器上的指标没有达到患者所需要的值,那么第二天还需要再采一次,这就要看个人体质和当时的情况了。
11月的天气,赵嘉鹏热得出了一身汗。还好,赵嘉鹏说:“一个志愿者哥哥一直在给我擦汗,陪我聊天,帮我度过那五个小时。”
从早上八点开始到大概中午一点结束,这是一段考验人身心的时间。
下午一点下了病床,大概过了十多分钟,经过简单休整,赵嘉鹏身心基本平静下来,想好给接受捐献患者的鼓励性留言,便去录了视频,随后又接受红十字会的慰问,接受采访……
这一下午,赵嘉鹏感觉好困。四点来钟,赵嘉鹏走出医院大门。他要好好休养几天。红十字会很关心关爱这些志愿者,他们告知赵嘉鹏后面满半年、满一年都会再做身体检查,还有一个两年的身体状况跟踪,确保捐献者身体状况正常。
后来,有人问起赵嘉鹏捐献造血干细胞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赵嘉鹏说,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其实,只要看到赵嘉鹏就知道,这个高高帅帅的小伙子显然是个运动达人。但为了捐献时身体状况再好一点,捐献前的两个月他还专门去健身,做好身体储备,保证体质良好。赵嘉鹏告诉大家:“体质不好的话捐献的过程会相对难过,捐献者有个好的体质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是抽血,对身体当时的短暂损伤还是有的,但只要是正常身体都可以恢复得挺好。”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是为别人做一份奉献,还是对自己,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才能做想做的事情。赵嘉鹏还记得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当时跟他讲过,身体条件好的人采集过程基本没什么感觉,有的小伙子捐献完下了床还能做俯卧撑呢,而一些身体较弱的人承受的精神压力比身体强健的人大得多,因为他们采集的时间可能更长,内心更煎熬。
疼痛跟心理压力也有很大关系,心理压力大会增加疼痛感。因为刚开始针扎进去所有人都会感觉微痛,如果身体不在意这事的话就可以将疼痛感忽略掉,如果有人一直在意这事就会把它转化为心理压力,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想,不断积累,就会越是到结束前越是心理上坚持不住了。
即便像赵嘉鹏这样健壮的小伙子,到了最后也会产生焦躁感。他说:“最后阶段我只盼进行得更快些,因为那十多分钟之后存在着不确定性,也就是不清楚结束后是否能达到指标,即便抽血停止,还得用五分钟把整个机器里的血输回去以后,再把机器停下来,然后才能真正结束。”过硬的心理素质是要有的,强大的毅力和强健的体质一样重要。
让爱延续
赵嘉鹏身体恢复得相当快,周四捐献,下一个周一就去上班了。对于这点,他非常自豪。他也好,妈妈也好,从没担心过捐献造血干细胞会影响自己身体,因为他们很清楚,造血干细胞具有高度的自我更新、自我恢复能力,捐献造血干细胞一到两周内,血液中各种血细胞即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有人问赵嘉鹏:“一年之后你还会再献血吗?”赵嘉鹏爽快而笃定地说“当然”,但在目前的研究生阶段,他要先专心致志地将手头事情做完,工作之后计划每隔半年献一次血。赵嘉鹏说,牺牲个人正常学习和工作去做公益是违背初心的,如果自己的事都做不好还去帮助别人这不太现实,就像捐献的前提是自己要先拥有一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就不会去麻烦别人了,然后还可以帮助别人。
这一次捐献造血干细胞,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所的老师们是相当支持的,同学们对此多有称赞。赵嘉鹏将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看得很平淡,也不太愿意张扬,在他看来,做好事本无需张扬。但这次经历是令他振奋的,他说:“我读本科时一直想去献血却没有机会,机缘巧合,大学毕业的日子赶上一个机会,又极其幸运地在半年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这很棒。”
一般能够去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基本具有日常的公益心,赵嘉鹏在读本科时就是大学生志愿者。现在大学校园里做公益的学生特别多,学校每次组织志愿者活动,收四百人的话就会有一千来人报名,组织者只得在群里发问卷表,依照先到先得的规则来选取志愿者。赵嘉鹏说:“我们当时学校还组织种树,学生都乐意去做,包括去社区组织志愿活动、汇报演出之类的事情都很热心。”
说起这些,赵嘉鹏脸上写满自信,他的谈吐中透露着阳光、涵养和知性,完全不是想象中的这一代被幸福宠坏了的孩子模样。他说他的同学们也是这样,关心社会、热心公益,有自己的理想和思考。这是令人欣喜和欣慰的,国民素质整体提升的号角被年轻一代吹奏得响亮而悠扬。那是希望之声。
对于别人的讶异和夸赞,赵嘉鹏说:“平常我观察或者自己思考,认为主要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心思才可以放到物质以外的更高处,做公益的人就多起来。经济跟科技发展水平很重要,先有物质的逐渐丰盈才有精神上的良好转化,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积累,一个人连生活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不会有额外的心思去做公益,主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意愿就要小得多。”
赵嘉鹏相信,我们都相信,随着社会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公益之心会一代一代不断地壮大,爱会流动起来。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